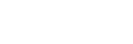著作权法、影视产业与市场控制史
导读:如何理解版权?回答这个问题在当下显得尤为迫切。在中国文化产业相关话语中,版权被置于了一个不言自明的超然位置。重新思考版权,其必要性不仅在于反思“版权是对文化产品创造者利益的保护”这样一种被常识化了的预设;还在于,当整个广电行业在言必谈IP之时,对版权与产业发展的关系进行梳理,并纳入新的讨论之中。本期批传公号特别推送一篇中国台湾学者的文章,从社会权力关系的视角理解著作权,并跨时性地检视台湾著作权规范发展前后产业市场秩序与利润分配的改变,探讨著作权与影视产业发展的关系。
著作权与台湾影视产业的政治经济分析:著作权法、影视产业与市场控制史
摘要:文化资讯商品的特质之一即其公共财性质难以排除他人之使用,因此著作权法制被创造,并用以保障著作权所有者得以获取其产品之市场独占利益。但随着著作权法制牵涉的商业利益越来越广,其也逐渐成为控制产业、市场、影响市场竞争、并进行水平与垂直整合之手段。本论文以跨时性之历史分析,探讨台湾影视著作权法制化后相关影视下游产业版权化后产业市场秩序之改变,以及版权化如何改变上下游,甚至影视产业间市场利润之重分配,以检视著作权对影视产业市场的真实作用与意义。
关键字:市场控制、市场整合、利润重分配、著作权、影视产业、独占
一、导论
每一个商品化过程均执行了资本主义资本积累之目标,将使用价值转换为交换价值,但,这个实现交换价值的目标究竟是透过何种手段来达成?以文化资讯产品来说,由于深具公共特质,而科技的进步又使其再制成本(边际成本)、传输成本越来越低,这些力量均使得文化商品化出现了实际的困难(Vaidhyanathan, 2001/陈宜君译,2003;Bettig,1996; Winseck, 1997),更遑论要打破民族国家的地理疆界与政治主权,建立起一套国际实现的体制。为了解决此困境,资讯与文化商品的提供者必须采用一些手段来打破文化商品的公共特质并控制科技造成的利益损失,这些手段包括借由国家力量介入立法给予资本家独占性地控制其文化商品供给与流通的权力,使资本家能借由此一独占权力得到独占性经济利益,并控制下游市场之利益分配,而此一保障独占权力的制度也就是著作权(Lessig, 2004/刘静怡译,2008;Gandy, 1992;转引自Bettig, 1996; Garnham, 1990;转引自Bettig, 1996)。著作权是当今建立文化商品市场秩序的重要规范,规定了凡属文化、艺术、科学、以及之后发展的影视、资讯等智慧创作商品商品化之原则,并规范了文化市场的运作规则,保障文化商品其市场价值得以实现,不被袭夺(Bettig,1996)。
观察著作权规范对产业与市场之影响,三种意义或作用逐渐浮现:一、著作权是影视文化商品化与实现独占利益的手段,用来保障著作商品的交换价值,以达到垄断性利益、市场利益重分配及资本积累之目的;二、著作权也演变为拥有著作所有权之影视中上游集团控制产业市场秩序、影响下游产业之市场竞争,并借之整合下游市场之工具;三、著作权法制本身即为一种意识型态,用以正当化著作权制度下不平等的市场关系。从台湾影视产业发展历史来看,台湾影视著作权法制化大致上是在1985 至1993 年间,一连串台美著作权谈判及美国特别301 法案压力下才逐步成形,而其中包括录影带出租业、MTV 视听业、影碟租售业与第四台及有线电视等四产业因时间因素,最明显经历版权化后产业市场之重大变革,而此四产业也是1985 至1993 年台美著作权谈判最主要的议题重点。
因此本论文以上述影视产业为观察,采取传播政治经济学取径之历史分析法,以跨时性之研究,佐以产业资料研究与深度访谈,来探索台湾著作权规范发展前后产业市场秩序与利润分配之改变,及检视著作权如何成为干扰市场竞争之手段,并作为影视中上游产业控制与整合下游流通市场之工具,借此呈现著作权法制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下之真实面貌与意义。
二、文献探讨
所谓著作权法乃是将文学、艺术、科学、音乐、影视等创作活动导入市场经济的法律,它赋予著作权人控制其著作市场的权力,借由独占性与排他性,以取得消费者给予其著作产品的市场价值(郑中人,1996;Grosheide, 1994; Latman & Gorman, 1981; Stewart, 1989; Winseck,1997) ,因此著作权与文化、资讯的商品化息息相关(Edelman,1979)。探究著作权法的起源,乃由于文化创作产品具公共特质,而复制科技的进步又使其再制成本(边际成本)、传输成本降得越来越低,这些力量均使得文化商品化的过程出现了实际的困难。为了解决此一问题,资讯与文化商品的提供者必须采用一些手段来打破文化商品的公共特质与控制科技造成的利益损失,这些手段方法包括借由国家力量介入立法给予资本家独占性的生产与供给文化商品的权力,使资本家能借由此一独占权力得到独占的经济利益,而这种保障独占权力的制度也就是著作权(Gandy, 1992;转引自Bettig, 1996; Garnham, 1990;转引自Bettig, 1996)。亦即,著作权乃基于著作所有权人拥有排除他人使用、生产、甚至贩卖其著作权商品的操控能力,而此一独占权力乃为了实现著作权商品在市场中的交换价值与独占利益,以保障资本家投入生产的利益不受损害,进一步实现资本积累(Bettig, 1996)。
但随着著作权法制牵涉的商业利益越来越广泛,商业化趋势越形尖锐,著作权的真实面貌早已非单纯保护创作者与著作权人,也失去原初鼓励创造、科学、与民主之理想,而是为著作产出流通利用相关的利益团体服务(赖文智、王文君,2007;Vaidhyanathan, 2001/陈宜君译,2003),而著作权商业化趋势倾向成就特定利益阶级、大型企业与财团,轻忽公众使用并使创造者个人渐行退位,且在商业利益团体压力与推动下不断扩展,已使得文学、音乐、影视、资料之内容、所有权、控制、转让甚至使用,都日益集中化,不但限缩创作权能,对社会文化也产生了明显的支配与钳制,成为控制文化如何使用之力量的集权化状态(Lessig, 2004/刘静怡译,2008;Vaidhyanathan, 2001/陈宜君译,2003),如Lessig(2004/刘静怡译,2008)指出,内容产业的集中化、新科技的使用、以及著作权法制扩张使著作权管制力量转移到少数企业手中,且这三股力量交互作用,使得历史上头一遭极少数集团能借由法定权利,对人类社会的文化发展掌握了强大的控制力量,因此他建议缩小对著作权的保护范围,以解决此一文化控制与集中化逐渐增加之情形,以免威胁民主论述、学术研究、文化进步与资讯自由流通。
而除了造成上述之文化集中化趋势外,著作权也是一影响市场竞争,控制下游流通、映演市场的重要手段,借由此一工具,著作权所有者得以左右市场利益在上下游产业、甚至不同国家间之分配(冯建三,2008)。从美国影视产业历史来看,握有片源的发行商经常对戏院业者予取予求,采行整套订购(block booking)和盲目购买(blind bidding)等不平等条约(李达义,2000,页115-116)。而以美国的录影带业为例,包括影片发行录影带的权利采公开竞标,“让收购影片的录影带发行权就像好几个饿昏的人抢食一份晚餐,不断抬高授权价格”,以使商品利益往市场上游流动(Wasko, 1994/魏玓译,1999,页162)。或如美国有线电视历史中,上游片商发展出的“独家播映权”,引发主要的电影付费频道之间的争夺战,并使电影付费频道变成与上游特定片厂形成专属关系,防止了有竞争力的新付费业者的诞生,致使付费有线电视频道市场因此变成寡占结构,而既有业者更因此被陆续整合进好莱坞体系中(张时健,2010;Wasko, 1994/魏玓译,1999;Litman, 1998)。另外,包括节目供应者与有线电视系统之间的整合,也使得节目供应者可以刻意不提供频道节目给敌对系统或新成立的系统,借以影响市场竞争(Wasko, 1994/魏玓译,1999)等等。
另外,借由界定不同流通管道的不同著作权授权类型,并控制其授权以及发行映演的时间顺序,使上游著作权所有者/片商得以挑起不同流通映演科技管道之间对发行时间早晚之竞争,砸下更多资本去抢更早的发行权,因发行映演顺序事关该流通映演产业对消费者之吸引力,进而影响其在整体影视产业中的竞争力。而借由不同发行管道其发行映演时间顺序之控制,也可以让影视内容生产者针对不同偏好及不同付费能力之使用者给予差别性定价,以达到利益之极大化(Bettig, 1996;Wasko, 1994/魏玓译,1999;Waterman, 2004),因此,影视内容著作权所有者/片商也借由这套授权机制来控制中游代理商与下游流通映演业者,以进行利润重分配,并借此建立较符合著作权所有者/片商利益之产业与市场秩序。
最后,著作权也导致影视产业上中下游权力之失衡,使上游业者得以借由版权掌握而向下整合、控制中下游业者,影响产业之均衡健全发展与市场竞争之多元性。例如从好莱坞发行与放映业者的对立历史来看,下游的放映业者较常处于弱势,由于发行商或单一公司经常独占控制了片源,或几家联合垄断市场,故而掌握了戏院命脉(李达义,2000)。进一步探究美国的例子,好莱坞核心集团借由集中化、规模经济与著作权法制强化对影视生产之控制,但在生产控制日渐完成,跨国影视集团成为国际影视产品主要喂食者后,影视文化流通管道的控制变得更为重要,其重要性甚至胜过对生产层面的控制,因其才是交换价值真正的实践场域(李达义,2000;Garnham, 1983;转引自冯建三,1992;Murdock, 1980;转引自冯建三,1992)。如美国在1948 年派拉蒙案例后,好莱坞片场制度瓦解,之后成为透过资本供给,将生产活动外包的生产形式,除增加生产弹性、生产效率与内容创新外,借由仍牢牢控制的影视产品版权与发行系统,不断开发整并新映演通路(独立电视台、有线电视、无线电视、卫星电视、录影带出租业、戏院),掌握多映演的销售流通通路,以完成资本对发行与映演部门之整合、集中与控制(张时健,2010)。以上也再次显示,著作权除实现所有权人的独占性利益外,更负有产业市场控制、下游市场整合、与利益重分配的目的性作用。
三、著作权与有线电视产业
1985 年著作权法确认有线电视的播送行为应受著作法公开播送权规范,以及1993 年有线电视法通过,《有线电视节目播送暨暂行管理办法》公布实施,有线电视播放的软体节目依法均需取得著作权人授权后方可播送。而随着新科技的发展,1991 年后,卫星传输节目软体的供应形式以及集团化的节目供应逐渐取代传统第四台播放录影带、影碟的跑带形式,成为有线电视系统节目供应的主流(管中祥,1997),因此在1993 年有线电视版权化与合法化工作完成后,有线电视与卫星频道供应者间的版权交易与权利金生态遂成为有线电视产业主要的著作权问题来源。
有线电视系统与频道节目供应者的版权关系复杂多变,大致上可区分为四个历史阶段,首先(1979-1993 年)是有线电视尚未版权化以及频道免付费时代;第二阶段(1993-1996 年)是有线电视系统版权化、合法化后,下游系统市场一区多家进行恶性竞争,使上游频道业者趁势哄抬频道版权价格,引起系统业者与频道经营者对立之时期;第三阶段(1996 年-2000 年),有线电视整合完成,系统水平整合、分区独占,全台湾系统分为和信、力霸以及独立系统三大势力,而频道方面则约有五大集团掌控了市场上主要的频道,其中力霸、和信不但是五大频道商之一,也是三大系统之一,垂直经营频道与系统,故此时期系统业与频道商势均力敌,又相互垂直整合,因此虽然境外频道因下游市场独占致使涨价优势不在,但起而代之的国内集团代理及自制频道占了垄断优势,而有涨价空间,而这个涨价的成本自然是转移给分区独占经营系统下的消费者,形成系统与消费者的价格战争。第四阶段(2000 年后至今),随著有线电视生态逐步成熟,有线电视与卫星频道供应者间的版权交易与权利金问题进入稳定期,频道及交易价格均不易变动,但独立频道生存空间狭窄。
(一)1979-1993 年:系统播放侵权带、卫星溢波与频道免费时期
在1979 年至1993 年间,时称第四台的有线电视系统播放的节目有三大类:一是播放侵权的影带影碟节目,二是播放他国卫星溢波至台湾的卫星频道节目,三是针对台湾播放的免费卫星频道节目。
1. 播放侵权的影带影碟节目
播放侵权与盗版的录影带节目早自1979 年就已出现(管中祥,1997) ,且在1992 年以前一直是有线电视系统节目播放之主要生态,第四台播放侵权与盗录片除了威胁著作财产权人之经济利益外,其播放未下档的电影严重影响了电影业与录影带业的生计,并破坏了影视产业的发行播放流程。因此约从1984 年起,即引发电影业者及录影带业强烈反弹,1985 年,有线电视应受著作权法公开播送权之规范受到司法机关确认,加上1990、1991 年后陆续而来的美国影片公司及美国政府贸易压力下政府严厉的取缔,使第四台业者从1992 年开始寻求录影带节目的公开播映授权(王保宪,1992 年5 月29 日;林浚南、陈宗仁,1992 年6 月12 日;陈宝旭,1992 年5 月29 日),1992 年6 月第四台业者与最大的录影带发行公司标致影视签约取得录影带节目公开播送版权(王保宪,1992 年6 月26 日),此时节目虽碍于授权权限多以国内影片为主,但第四台已逐步脱离播放侵权影带时期。
2. 播放他国卫星溢波至台湾的频道节目
1984 年日本发射樱花卫星,即有台湾民众以小耳朵接受其溢波讯号从事收视行为,1985 年「百合三号」包括NHK、WOWOW 频道等节目讯号溢波至台湾,第四台业者遂加装碟形天线接收讯号,并转播送供收视户观赏,使第四台开始正式增加卫星节目服务(曹竞元,1993 年8月24 日;冯建三,1998;管中祥,1997),1992 年2 月,日本商业电视卫星「超鸟二号」升空,并提供十个频道的卫星电视节目,由于超鸟二号上有美国CNN、Star Channel 等频道,其被台湾第四台接收转播的行为引发美国业者抗议,并要求日本卫星电视公司加强锁码,保护美国影视业者权益(郑士荣,1992 年5 月26 日),此后第四台便无法再公开自由地接收卫星溢波的美国节目,而接收卫星溢波合法性的问题也被正式提出。1993 年7 月司法院解释认为播送卫星节目并不违法,引起美国贸易代表关切,1993 年9 月,内政部汇整各单位意见做出第四台接收并转送卫星节目之行为属于「公开播送」,应受著作权法规范,并在1994 年3 月「台美智慧财产权谘商」中台美双方得到播放溢波的美国卫星节目系属违法行为之确认(叶玲吟,1997)。而日本的卫星节目也因1993 年有线电视法与暂行管理办法规定,第四台的节目非经授权许可,不得擅自播出,因此日本NHK 等卫星节目于法都不能再播出(曹竞元,1993 年8 月24 日),正式宣告有线电视接收溢波频道时代的结束。
3. 播放免费的卫星频道节目
从1991 年开始,一些意图进入台湾有线电视市场的频道如卫视中文台、BBC 与TVBS 等均以免费方式提供有线电视业者自由播送,以加速扩大频道普及率(郑士荣,1992 年9 月25 日;卢悦珠,1991 年10 月18 日),并培养观众消费其频道之习惯与依赖性。但1993 年初卫视增设七个新频道,并开始表明每户每月拟收105 元月租费,虽然卫视中文台仍是免费频道,但却成为拉抬卫视其他频道搭配销售的手段,此举引发有线电视业者抗议与酝酿拒播,并争论究竟是系统应付卫视收视费亦或卫视应均分其广告收益给系统业者(郑士荣,1993 年1 月9日),然最后卫星频道收取收视费仍成为主流,揭示了免付费时代之结束及权利金战争时代来临。
(二)1993-1996 年:频道商与系统业者间的权利金战争
1. 付费频道进入台湾市场
自1993 年开始,随著有线电视合法化与版权化,付费卫星频道陆续进入台湾,首先是1993 年初卫视频道开始收费,6 月和信取得CNN代理权,成为第一个取得国际性卫星电视播映权之业者(曹竞元,1993年6 月4 日),之后即带动一连串频道进入台湾市场效应,7 月美国体育专门频道ESPN 由亿通代理来台播出(王介中,1993 年7 月17日),9 月HBO 授权年代代理进入台湾市场,同月由年代、香港无线电视等合组的TVBS 也正式开播(曾竞元,1993 年9 月29 日),而国内频道国兴、万里达与泛卫公司等在8 月底合组“台湾卫星频道经营联盟”也进入有线电视市场(王介中,1993 年8 月29 日)。之后国内频道、境外频道纷纷开播,而负载越来越多频道的有线电视,经营成本也节节高升,但在有线系统市场高竞争压力下,不得不持续增加频道数目,造成频道数目膨胀、同质性高及资源浪费等问题。另外,一些受欢迎的境外频道在国内代理权竞争下拉抬权利金,及利用准独占商品优势不断提高授权价格,使下游系统业者与上游频道商、代理商进入对立冲突状态。
2. 系统业者与频道商的权利金战争
自有线电视版权化后,节目与频道权利金节节高升,而涨幅之高又以境外频道为翘楚,且境外频道背后的控股公司多是美国前十三大的媒体企业集团(王介中,1993 年7 月28 日;吴秉锴,1996 年12 月6日;黄西玲,1997)1994 年3 月,为抗议年代代理的HBO 频道售价过高,部分有线电视业者集体罢播TVBS,同月25 日,卫视宣布推出电影台,并开出年权利金一亿六千万高价,震惊业界,随即并引发系统业者抗议,然最后仍由“第四有线产业公司”以高于原价的一亿九千万取得代理(《卫视电影频道按钮开播 两亿美元》,1994 年4 月20日),但部份业者如“有线电视播送系统联合会”所属会员仍拒播卫视电影台,并停播卫视所属频道以示抗议(曹竞元,1994 年4 月27 日,1994 年3 月25 日;冯建三,1998)。
1994 年9 月因HBO 与TVBS 频道调高价码,引起台北县有线电视业者抵制停播部分频道三个月(石先登,1994 年9 月6 日),12 月北县有线频道经营者筹组购片联盟,以集体行动对抗软体供应商不合理的涨价(袁延寿、石先登,1994 年12 月23 日)。1995 年初有线电视业者持续以停播TVBS 来抗议年代代理的五个频道价格过高,但频道代理商表示频道涨价乃授权权利金飞涨所致,代理商迫于生存才提高售价(曹竞元,1995 年10 月31 日)。而据公平交易委员会1995 年调查,频道费在一年间上涨25.7%,居当年所有著作物商品价格涨幅之冠(张玉文,1995 年8 月15 日)。
1996 年涨价与断讯戏码重复上演,元月七十六家系统业者为抵制年代七个频道大涨25-50%,其中尤以HBO 涨幅最高,涨至每户每月一百八十元月租费,系统因此决定结合下游业者力量,统购节目(郎亚玲,1996 年1 月28 日;彭淑芬,1996 年1 月26 日)。同年8 月,境外频道代理权更换之际,年代表示因HBO 授权权利金大涨35%,金额高达两千八百万美元,年代无力代理,因此决定放弃争取HBO 代理,并呼吁系统业者拒播(彭淑芬,1996 年8 月14 日),但HBO 却表示是代理商从中剥削,并宣告将规划成立直属的台湾代理公司来经销HBO 频道(喻靖媛,1996 年9 月12 日)。同年12 月,由于频道代理商激烈争夺境外卫星频道代理,使迪士尼、HBO、ESPN 等著名境外频道以竞价方式不断哄抬频道代理金价格,并各开出美金五百五十万、两千七百万、七百万的高价(曹竞元,1996 年12 月2 日),然而代理商不以为意,以ESPN 频道为例,因超视与木乔之竞争,使ESPN 以高出原先价格一百万美金的八百万美金天价卖给木乔传播(喻靖媛,1996年12 月10 日),将巨额经济利益送给美国影视集团,严重威胁国内影视资源与影视环境之健全发展。
而针对有线电视系统频以断讯为手段来反制频道涨价行为,新闻局则以违反消费者保护法第36、38 条警告,要求有线系统恢復HBO 等境外卫星频道讯号,否则将处以罚锾(陈民峰,1997 年7 月12 日),对于新闻局不过问境外频道在台湾进行频道垄断与哄抬价格行为,反而回过头要求系统业者复播境外频道,引起了国内系统业与频道业者不满(张文辉,1998 年1 月4 日),认为新闻局昧于境外频道独大事实,帮助外商打压本地产业发展。而1993 至1996 年间因高昂权利金使有线电视系统业者平均报酬严重亏损,致使一些独立系统业者开始向多系统经营者(Multi-System Operator, MSO)者靠拢,希望透过MSO 统一购片,取得更多折扣降低内容成本,此举也促成有线电视系统市场之加速水平整合。
(三)1996 年底至2000 年:有线电视整合后之著作权交易
1996 年后,有线电视水平与垂直整合脚步越来越快,而有线电视整合与版权交易有着双向关系,首先是有线电视上下游产业的水平与垂直整合经常以频道的版权交易作为市场整合手段,二、整合后的有线电视生态又会影响上下游版权交易生态,因此有线电视整合与版权交易处于一种变动辨证关系。有线电视产业整合常用的版权手段包括联卖、搭售、频道不卖、系统不买、区域独家授权、差别定价、统购等。有线电视产业整合与版权交易之关系影响综述如下:
1. 版权交易成为有线电视市场的整合工具
(1)频道商的水平整合与竞争手段:套装搭售与联卖
将频道套装贩售始自年代国际,由于过去拥有强势频道HBO、TVIS 职棒节目,拥有绝对的群众基础,于是年代以强搭弱,规定系统台业者必须购买年代整套节目,将收视基础不佳频道一并推销出去,结果导致业界另外四大频道商和信、力霸、木乔、佳讯等纷采频道套装贩售,要求系统业者消化掉业者拥有的所有频道;五大频道商所有频道数高达五十个左右,在频宽有限情况下,严重排挤独立频道生存空间。另外,五大频道商套装搭售的频道采高价策略,五家频道商频道台面价格总计高达三百元,超过业者所能负担的购片成本范围(喻靖媛,1996年12 月24 日)。
除了自家频道套装搭售外,频道业者也进一步进行水平连结,以联卖频道方式打击竞争之频道商,以图垄断市场,并保障自家频道普及率与出售率。联卖虽不及搭售普遍,但其排挤效应远高于搭售。以早期而言,和威(和信)与木乔即曾联合销售旗下二十八个频道,并遭公平会警告勒令停止联卖行为(《联卖频道违反公平法 和威、木乔移送法办》,1998 年8 月)。
(2)频道商垂直整合手段:不卖频道、差别定价
频道商为了向下整合系统业者,经常使用不卖频道与差别定价的方式来逼系统业者就范,合并至所属系统之下,以强化频道商对下游的整合与控制,若系统业者坚持独立经营,即要面对重要频道消失,丧失与其他系统竞争之能力,或以高于其他系统的价格买到频道,在购片成本上与其他系统业者处于不平等竞争状态(陈民峰,1997 年3 月25日)。
(3)系统业的水平整合、竞争手段:统购、争取区域独家代理
系统业者的水平整合与统购行为一方面有制约上游频道业者漫天要价效果,但另一方面对独立系统经营者而言,却造成购片成本高于统购系统的不利因素,加之以系统朝集团化发展,联合购片议价筹码高,被排挤在统购之外的独立业者其竞争空间明显压缩。
另一方面,区域内强势的系统业者要求频道商售予其区域独家代理权,在特定区域内以其频道独家代理为筹码,要求其他系统必须向其购买节目,并配合其交易条件,等于授予个别系统频道垄断地位,增加其吞并独立系统之筹码,影响系统业者间的公平竞争(《整顿有线电视市场 公平会发威 要求频道商不能与新视波订定代理权契约》,1998 年2月6 日;夏淑贤,1998 年1 月22 日)。
(4)系统业的垂直整合手段:不买、不播频道
系统是频道重要通路,系统购买也是实现频道经济价值的方式,因此当下游系统市场整合完毕,有足够力量反制频道,不买或拒播某些频道,系统则反而拥有了影响控制频道市场之力量。但下游向上整合的例子较少,至多是上下游相互整合,进而以控制通路方式排挤部分上游频道的生存空间,以达整合上游市场之效。
1995 年台湾有线电视频道快速增加,一年即增加四十余台,之后每年增加约二十多个新频道,使得有线电视多系统经营者(MSO)可以透过系统集团整合频道集团,如东森、纬来透过系统市场的定频垄断力,扩大其在频道市场的占有率(曾国峰,2009)。1998 年中,两大频道兼系统集团,力霸、和信一改对立姿态,在上下游市场互相合作,首先和信、力霸相继入股25% 至频道代理商木乔公司,并相互保证双方系统(共47 家系统,占台湾系统通路约55% 至60%)都购买力霸、和信与木乔频道,总计频道数高达四十二个,称之为频道“三合一”大整合。而其余有限的频道数约三十个,有六十多个频道必须竞争三十个频道空间,因此其他频道商莫不纷向和信、力霸示好靠拢,或直接整合至两大集团之下,以使自己的频道能进入“有限”电视市场。而掌握系统通路的东森集团也提出“超商”经营概念,认为频道商应付系统业者上架费,来买到一个频道位置,以利其播出,一改过去系统商付频道业者版权费之观念(王玫玲,1998;张义丰,访谈,2010 年9 月3 日;陈镜明,访谈,2010 年9 月9 日;曹竞元,1998 年10 月8 日;游醒人,1998 年7 月,页37)。
2. 有线电视市场整合后的版权交易
有线电视系统水平整合、分区独占后,频道版权交易的权力关系也随之改变,对于上游频道经营业而言,下游的整合使得其对抗力量增加,频道商转处于不利位置,但系统整合也使国内有线电视产业得以有效对抗跨国影视频道资本,不再任由境外频道商利用独占地位与代理权之恶性竞争来漫天喊价、牟取暴利,浪费国内影视资源,另也减少了跨国影视集团借由控制频道供给进行对下游控制之可能。但系统业者与频道业的水平垂直整合,确实也产生打压独立频道生存之现象(黄治,访谈,2010 年9 月9 日),但系统业的独占地位若不受公权力之监控,也将产生消费者与业者权力失衡现象,因此行政主管机关介入以规范独占事业体并避免有线电视集团滥用独占地位,妨害公共利益伤害消费者,是有线电视系统市场整合后的重要议题。
(四)2000 年后至今:法规介入,有线电视版权交易进入稳定期
有线电视至2000年代,系统已由原本的一百五十六家整合至不到六十一家(2009 年),且历经所有权递嬗,由四大系统业者中嘉、凯擘、台湾宽频、与台固媒体垄断,超过三分之二的地区为区域独占(简旭伶,2010 年6 月17 日;曾国峰,2009)。在有线电视系统水平整合、分区独占状态稳定后,且新闻局自1997 年于《有线电视节目播送系统暂行管理办法》制订审议播送系统费率法源,以及1999 年有线广播电视法规定有线电视费用交由各地方政府设立费率委员会,依据新闻局审议委员会所定之收费标准來核准公告后(钟瑞昌,2005),有线电视系统无法因其独占地位任意收取过高费用,使用者端的费率被限制,另外频道变动还需主管机关审核,加之以有线电视系统与频道及频道代理也因各自水平整合,甚至部分垂直整合而达到势均力敌,甚至系统商在授权金谈判上更具优势后(简旭伶,2010 年6 月17 日),版权交易与权利金问题正式进入稳定期,前八十台频道甚少变化,价格也几乎依循往例或固定机制,改变越來越少(陈信维,访谈,2010 年8 月18日;张义丰,访谈,2010 年9 月3 日)。2001 年前常见的,因市场整合、版权交易纠纷导致之系统业者断讯频道讯号之风波也逐渐变少,并购、外资与数位化牛步等议题取而代之,成为有线电视较被关切的问题。而近年有线电视系统订户每月缴纳费用依不同县市约在五百五十至六百元之间(钟瑞昌,2005),其中购片支出约占两百四十元,每频道可获得每户二、三元至数十元的频道分销费,一年收入从七、八千万至三、四亿不等,但部分独立或小频道,如八十至一百的频道,反需支付上架费,系统每月也因此额外获利数千万元(曾国峰,2010;张义丰,访谈,2010 年9 月3 日)。
总体而言,有线电视版权交易历史中,一开始如同其他影视产业,均面对上游代理商与影片商利用独占供给地位,进行不公平交易与订定独占价格等现象,而在下游业者高度竞争时期情况也愈形恶化,代理商与影片商的剥削较严重;但有线电视不同于其他影视下游产业,其经营成本、规模巨大,属自然独占事业,因此下游业者间的整合很快即完成,使代理商与影片商滥用独占地位的效果大打折扣,另外加上有线电视的软体來源-频道经营者,相较其他影视产业的软体來源,其多元性高,不乏有国内频道可以与外国频道竞争,甚至由于频道数目多,相互替代性也高,使得代理商与影片频道商的供给独占地位不稳定,故有线电视版权发展对产业影响也就异于其他以中小资本为主的影视下游流通产业。
四、结论
(一)著作权实现影视上游产之独占价值
著作权之建构乃为让著作所有人拥有排除他人使用、生产、及贩卖其著作产品的控制力,而此一排除权力乃为实现并提高著作商品在市场上的交换价值甚至独占性价格。就影视产品的著作权商品化过程來看,在实施了各类型著作权保护规范后,由于著作权确保了上游,特别是跨国影视生产集团的独占地位,中下游的代理、流通产业之版权(购片)成本均大幅提高,又加上上游产业让版权交易处于不稳定的高度竞争状态,一两年即换约一次,并以竞争程度高之竞标方式决定授权,让台湾争取各类影视产品授权的代理商在高度竞争下将影视产品版权权利金追高,使拥有大量影视著作所有权之少数跨国影视集团实现数倍于其影视著作物独占价值之利益。然而,下游流通市场由于新媒介科技管道大量崛起导致激烈竞争,使下游业者无法将增加的著作权成本转嫁给消费者,造成下游业者生存空间萎缩,利润往上游重分配并集中,成为如业者所言:“面对市场端的业者都很惨,但影视上游却很OK”之现象(张心望,访谈,2010 年11 月19 日)。
(二)著作权成为市场控制之有效工具
著作权规范也实现了影视生产集团借由独占或控制产品供给及供给顺序來控制市场秩序之目的,各种著作权权利类型,如公开上映权、公开播送权、公开传输权、专有输入权(禁止真品平行输入)、或出租权与变相出租权等规范,给予著作所有权人,亦即影视生产集团削弱代理商权力、划分市场(亦即依消费者偏好与付费能力)以差别定价、并借差别定价來极大化其市场利益,并让上游集团得以借影视产品供给发行之时间顺序,來控制影视市场的秩序与利润分配,另也借此形成不同科技流通管道对映演时间顺序之竞争,让版权金再被争高,利润更向上游影视集团集中。以影片发行顺序來说,能否尽早发行关乎产业之市场竞争力,上游影视集团掌握此一权力,借由其对消费者消费能力及市场大小之评估,控制了发行顺序,使市场价值成为决定下游业者生存空间和竞争力,以及各种消费者其文化消费位阶的主要因素,消费能力越高(付出价格越高)与市场越大之产业,越容易取得较早发行之机会,而部分产业如MTV 视听业,由于其市场小,影视集团不欲其生存,因此其发行顺序不断被往后推延,打击了MTV 视听业之竞争力,加速其市场萎缩、衰亡。
(三)著作权成为影响市场竟争、进行市场整合之手段
著作权造成供给的垄断,加上著作物难以取代的独特性,使影视产业的上下游产销权力出现失衡。在上游业者处于较优势地位的状况下,著作权交易经常成为中上游业者借以影响市场竞争、控制并垂直整合下游业者的手段。其中发生在录影带出租业、影碟租售业与有线电视产业的例子,中上游的代理商(或频道商)常借由独占性的版权交易地位來图利其垂直整合的下游流通业者(如独家交易、差别定价、对独立业者刻意断片等),欲借此影响市场竞争,迫使下游业者纳入其集团,或借由强迫性的联营制度來间接达到整合控制下游市场之目的。在有线电视稍早之发展中,著作权交易也经常被用作频道及节目供应商以及系统业者间水平整合、竞争之手段,如频道商的搭售、联卖,系统业者的统购与争取区域独家代理等,都是欲借版权交易手段來达到打击竞争对手,进行市场水平整合之目的,其中如系统业者的统购,即造成有线电视系统加速水平整合之历史结果。而近年发展的中华电信IPTV—MOD,也因主流频道业者与既有有线电视业者垂直整合或利益共生,以缺乏著作权中IPTV 之公开传输权为由而不授权MOD,影响MOD 与其他影视服务提供者间之竞争力(张义丰,访谈,2010 年9 月3 日;陈镜明,访谈,2010 年9 月9 日)。
(四)著作权造成的市场发展之扭曲
而著作权除因法定给予之特权导致可预期的市场发展结果外(如国内影视资源、利润大量朝上游跨国影视集团流动及重分配),也有许多非法律预期或非法律允许的市场扭曲结果发生,挑战了社会与产业发展的公平正义原则。在台湾影视产业版权化历史,甚至在现今状况中,都可见上游业者(如发行代理业者)借著作权给予之独占地位迫使下游流通业者签署不平等契约(如高额签约金、预收款、搭售等)、订定不合理之授权价格、并利用告发与诉讼手段使下游业者陷于著作权官司威胁的恐惧中,进而借和解金以图利等均历历可见。如影碟发行代理业者扣押契约书使下游业者长年处于无授权的可被告之状态;录影带发行代理业者以刻意不发行产品,或因授权金太高默许出租店拷贝,引导下游在无产品可经营或受默许情况下诱使业者进行著作权犯罪,形成上游业者的不公平行为却致使下游业者犯罪之事实,挑战社会公平正义,更是值得深思。
(五)动态角力之可能与国家之角色
从本文所观察之四影视产业版权化后的产业市场发展來看,著作权所导致之上下游产业权力结构之失衡,往往在下游业者整合或采取集体行动后可能得以翻转,如有线电视发展历史所告诉我们的。然而,下游产业之整合与合作在下游市场属高度竞争状态时可能会升高其难度,并较易被中上游势力个个击破;此外,下游业者之水平整合可能涉及独占、垄断,需法律、政策等介入以保障终端消费者之权益,并引导产业朝向符合社会整体利益之方向发展。而下游业者在面对上游产业时之联合行为,也因易涉及限制竞争等自由贸易协定规范,容易演为国与国间之纠纷,因此通常需经公平交易委员会之同意核可,由国家在避免因国内代理竞价而抬高权利金,因市场不够整合而缺乏集体力量,使国内影视资源过度流向上游跨国影视集团,导致台湾影视资源贫弱,影响在地影视文化生产之考量下,由国家支持争取符合台湾影视产业健全发展利益的合理影视著作授权规范及价格。因此,本文也以为,为平衡国际间影视资源之流动,健全国内影视产业与影视生产之发展,国家的角色,在影视下游产业缺乏整合与过度竞争时,尤其显得重要。
节选自王维菁《著作权与台湾影视产业的政治经济分析:著作权法、影视产业与市场控制史》,原载于《新闻学研究》‧ 第111期‧ 2012年4月‧頁129-197
分享至: